社会学在中国:学科化的过程,也就是进入日常
原文作者|李培林
摘编|罗东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李培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
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科化过程,反映的是中国普遍的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而这种普遍的制度变迁,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洪流。社会学的学术制度,就像学校的制度、邮政的制度、铁路的制度一样,是一种现代化的“制度符号”,有了这些符号才能解读和延续现代化的“思想本文”。这些制度的酝酿、引入和建立,也许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甚至不经意的;随着时间的磨蚀和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人们或许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们最初所具有的意义;但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的确蕴含着观念的断裂、方法的创新和社会的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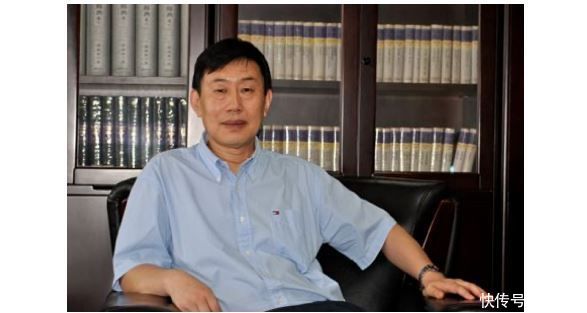
作者简介:李培林,1955年5月生,山东济南人,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书斋知识到现实世界的“生活”:现代社会学的兴起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制度变迁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制度变迁虽不像思想观念变革那么充满着论战的激情和攻守转换的戏剧性,但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变迁来说,它毕竟是显著的,具有思想符号和行为规范的普遍意义,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往往会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的变迁,是最大量发生的、最不为人所在意的和最经常、最持久也是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变迁。很多学者习惯于把思想观念视为比日常生活更深层的东西,而现代社会学方法的导入,将这一观念本身颠倒过来。
历史上的学者,似乎从来注重的都是从书本里寻知识,讲究师承关系,讲求思想渊源。学问的深浅,要看概念的锤炼功夫,要看能否从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发现新的微言大义,从而建立自己的知识话语和观念符号。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闲,大概应归于形而下的末流,不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东西。
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产生,是把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比较、分析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上来,它开辟了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观察中寻找学问的道路。做学问,要学会询问,这也许就是学问的本义。但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上还很少有人把今天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概括为一种做学问的路子。
法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勒普莱(F·Le Play,1806-1882)通过对工人家庭进行实地调查和个案调查获得的资料,在1864年写了《欧洲工人》一书,从而使他成为开创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最早的先驱之一。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等,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他在1895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使社会学在做学问的路子方面完全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列强拓展和维护殖民地的需要,人类学受到刺激而快速发展起来,对土著社会的关注使许多人类学家赴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实地调查,社会学的参与观察调查方法也因而进一步地发展了。革命的理论家为了理论的适用性,也很早就开始使用社会调查的方法。1845年恩格斯在24岁时,就根据实地调查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马克思在1880年62岁时还设计过一个长达100个问题的《工人调查表》。
社会学在中国: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
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中国的学者们这时才幡然醒悟,原来学问(尤其是解释具体社会现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的。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的运用,使中国学术的实践取向进一步强化。
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大概是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北京高校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组织)于1914-1915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此外,1923年,陈达指导清华学校学生调查了附近的成府村91户人家、安徽休宁县湖边村56户人家和学校雇役141人;1924-1925年,甘博、孟天培、李景汉在北京调查了1000位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和100个车夫家庭;1926年,孟天培和甘博以北京几家粮店的账簿、行会章程为依据,以若干家庭社会预算为参照,调查了北京1900-1924年25年的物价、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情况;1926-1927年,陶孟和采用家庭记账法,对北京48个手工业工人家庭和12个小学教员家庭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写成《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于193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