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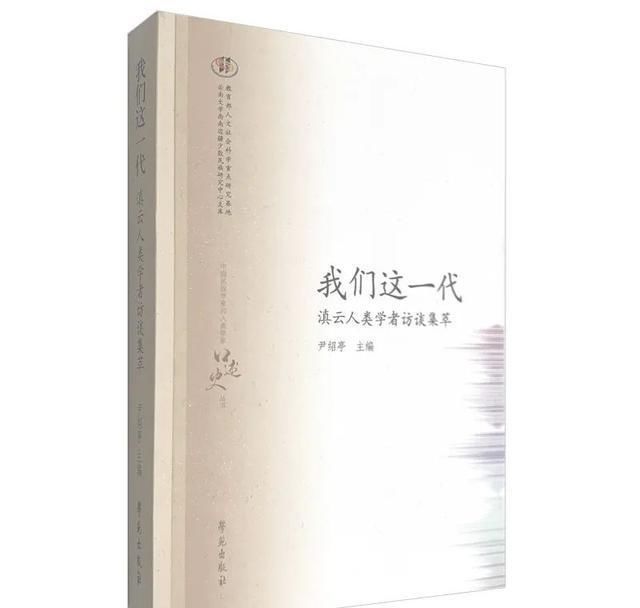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何翠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1993—2017年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17年6月底退休。她的研究开始于云南的景颇人,之后扩展到对西南作为一个“界域”探讨的关怀。从联姻价值与表演性的理论出发,其景颇研究一直以跨境的缅北克钦与中国景颇的文化议题为焦点;而她对西南的探讨,不是只有当代国界所画出的西南,或是历史间接统治下边疆意义的西南,而是在中国与高地东南亚之间的界域上活动,继而发展出自己生存之道的西南。
黄淑莉,台湾清华大学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2015年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自1999年首次进入苗寨进行田野调查以来,其研究对象一直是“苗/ 苗族/ 苗人”(Miao/Hmong)。其理论关怀着重在探讨沟通技术的社会效应,探讨口语和文字两种不同的意义媒介与苗人结群方式的关系,以及沟通技术的改变如何推动苗人社会变迁。她的研究主题分成两大类:一是与苗人传统仪式语言有关的研究,二是与苗人改宗与社会变迁相关的研究。
集体与跨学科的西南研究
黄淑莉:您在人类学界推动西南研究,乃至西南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不遗余力,能不能谈一谈这些经历以及对您研究的影响?
何翠萍 : 这个问题正好衔接你上一题与下一题比较理论性的讨论,触及我研究生涯中很重要的集体层面以及对区域研究的探索。先从经历谈起吧!
1990 年我进入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现在。民族所是一个全世界都算很难得的研究机构,最重要的是它聚集了一批具有很明确国际人类学理论视野和关怀的人类学学者。研究人员有做台湾山地与平地的南岛语人群,台湾汉人或中国文化与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研究的传统。我加入民族所队伍之际,正值台湾解严、逐步开启两岸学术交流的时期,也是民族所人类学追求与国际人类学(不仅仅是关注汉人社会研究之国际学者)直接接轨的时代。当时还有多位社会学学者与心理学学者。1997 年在李亦园老师的支持下,我与他开始在台湾清华大学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共同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的课程。从此我一直在台湾清华大学兼课,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西南与高地东南亚跨境人群”以及“界域人类学”课程,因此到现在总有硕士班或博士班做中国西南的研究生跟着我。民族所的研究环境与台湾清华大学的教职让我有机会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开展与国际及中国研究西南的人类学同行以及台湾清华大学学生合作探讨的可能性。1998—2001 年我在同事蒋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亚洲季风区高地与低地的社会与文化”主题计划中,主持了“交换、生命仪礼与人观:中国西南族群区域研究计划”;同时,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魏捷兹也在同一个主题计划中主持了“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计划。
我们两个计划常一起在昆明或南宁开年度会议,蒋斌也尽量参加。最令人感激的是,这两个计划也帮助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开展他们各自人类学田野的探勘;同时,也更大限度地让我们认识了更多西南研究的同行,并建立起与云南大学林超民和尹绍亭老师长远的合作关系。在我有机会与云南、广西及贵州的民族学学者一起做集体研究,同时开始带到西南做田野调查、撰写硕、博士论文的学生时,很自然地,不少主题都环绕在亲属、家屋民族志与仪式、礼俗的探讨上。这些经历让我不断扩展除了自己研究的景颇之外中国西南不同族群文化的了解。当然更可贵的是在学术道路上与同行培养的深厚友谊,及看到每位学生写出的硕、博士论文及文章。他们扎实的田野材料是我在思考区域性理论上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1988年9月在昆明当时的云南民族学院认识的景颇学生,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景颇菁英了另外,我认为任何人类学研究都不能没有历史的认知,而在我的人类学生涯中,最欢喜与历史学学者合作。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2005—2008年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David Faure)老师一起主持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历史人类学计划“土司的改宗——边境地区的地方神、土司世系与在地认同的维系”(Conversion of Chieftains—Territorial Gods, Chieftain Lineages and the Retention of Indigenous Identity in Border Areas)。这个计划不仅在研究上有很不错的成果,同时更可贵的应该是参与计划的个人,都与魏捷兹、科大卫及我三人有师生关系。正式展开计划之前,到计划结束后,每次开会又都各自有更多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人类学系所与历史学系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与同事参与。这当然也帮助我对中国社会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理解。我们这一群同事、朋友与师生,人类学训练背景者本来就从各自不同的研究地方与族群的田野来,通过这个计划,我们更小心谨慎地检视区域以及可能牵涉到更大片区历史的蛛丝马迹;而历史学训练背景者也走进田野批判性地收集、检视在各种史料中提到和没提到的材料,翻转、重新诠释他们在文本数据上看到的信息。
